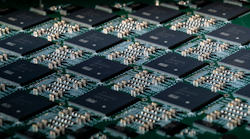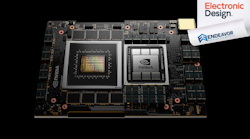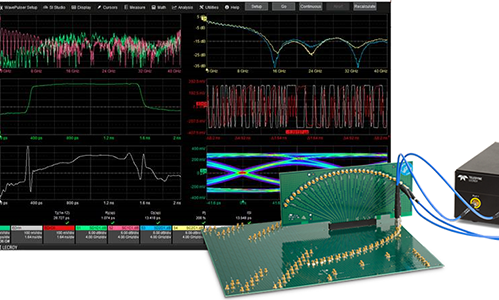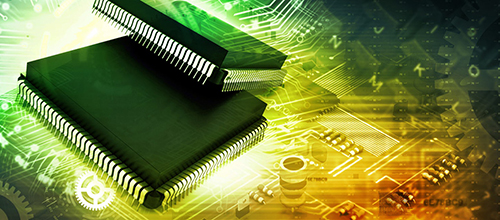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在线文章中(见“数字回忆的仓库火灾”),亚当·钱德勒写到一个事件的美国协会科学促进会,期间互联网先锋Vint Cerf”警告说,一个“被遗忘的一代,甚至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纪”,等待我们当数据腐败扎根和数字材料被新的硬件和软件研磨赛车。”
瑟夫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漫不经心地把所有的数据扔进了一个可能成为信息黑洞的地方。我们把东西数字化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保存它们,但我们不明白的是,除非我们采取其他措施,否则这些数字化的版本可能不会比我们数字化的文物更好,甚至可能更糟。如果你真的很在乎照片,那就把它们打印出来。”
想法不错,但是,唉,太迟了。我从1966年开始就一直在为出版物撰稿,唯一被存档的是我当时为RPI教授哈里·梅纳斯写的关于物理演示实验的描述。这些都印在书里了(物理示范实验,体积1和2).
不是有很多人想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模拟X-y绘图仪附件,用于摆脱战争盈伺服电机的架空投影机,但你永远不会知道新想法可能会让某人想到一天。
这就是我的重写本理论。在古代,节俭的人把旧的手稿刮干净,然后在上面写上新的东西。这就像瑟夫提到的旧数字媒体。令人高兴的是,有了旧的重写本,人们可以小心翼翼地读到过去作家们的潦草字迹,从而找到那些有价值的旧东西。这对于重复使用的软盘来说就不那么好用了,即使它被证明可以从一些磁场中提取真实的信息,那么旧的介质在哪里呢?需要一些真正专注于打包的老鼠来保存所有这些旧的软盘和备份磁带驱动器。即便如此,磁性介质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那么,展望未来,云是答案吗?瑟夫显然不这么认为。我想他会同意,无论我们建立了多少冗余,我们都是在熵的支配下,而熵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仁慈。
不过,CERF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如果有你真正关心的照片,打印出来,”他说。关键词有“你”。我们仍然有预先媒体经典的原因《伊利亚特》或者锡箔Bo Cuailnge是有人足够关心去学习它们并把它们传递给其他人。这就是梅纳斯教授在RPI所做的。他把这些基础知识教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工程师,而如今,这些工程师又将这些知识传递给了下一代。哈利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那些书——嗯,它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了。但那些关心和使用时代精神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媒体来对抗熵和传递信息的人,而不是媒体,才是我们需要继续前进的人。